演員:阿赫勒.里札夫(Agheleh Rezaie)
阿多甘尼.尤瑟夫拉茲(Abdolgani Yousefrazi)
伊朗 / 2003年 / 105分鐘
伊斯蘭教義下的廿歲女孩需要全身罩上面紗才能去上學…
◎ 劇情簡介
諾克奈是二十歲的阿富汗少女,她的父親總是要求她全身罩上面紗才用騾車載她去上學。但諾克奈不喜歡那種老式只唸可蘭經的學校,她會偷偷地掀起面紗穿上白色高跟鞋,再撐起一把洋傘跑到另一所正規學校上課。
學校的老師作了調查,有的學生將來要當老師;有的要當工程師,只有諾克奈和米娜要當女總統。因此老師要她們二人在學校舉行競選。
諾克奈的哥哥阿吉塔是卡車司機,但上一次出門後就沒有回來,嫂子雷諾瑪養了一名嬰兒,然而因戰爭家貧,嬰兒生病也無法送醫。
這一日從巴基斯坦來了一大羣難民,諾克奈好意引導他們暫住廢墟中,沒想到連雷諾瑪的住處也被人佔住了。諾克奈和父親雖然埋怨,也只好在三更半夜另覓他處。沒想到遇到軍隊臨檢,諾克奈懷中的洋傘差點被當成槍,所幸化險為夷,找到一架毀損的飛機,以機艙當作居處。
難民中有一名年輕的詩人慢慢喜歡上諾克奈,尤其諾克奈說她想當總統並需要一份演講稿時,詩人立刻為她找來比那奇-布托的講稿。為了在學校的競選,詩人還帶諾克奈去拍照。
詩人好幾次去學校接諾克奈,諾克奈雖然表示怕別人會議論,卻也喜歡坐上詩人的腳踏車奔馳在馬路上;但回家之前,諾克奈總會將白高跟鞋換回黑布鞋,並收起洋傘戴上面罩,以免父親生氣。
詩人為諾克奈洗了很多相片貼在廢墟的柱子上,諾克奈雖然驚喜但也急急制止,因為她畢竟無法向老父交代競選總統之事。而另一參選者米娜卻因爆米花機器爆炸而喪命,使得諾克奈失望到極點。
更令人難過的是父親終於獲知兒子阿吉塔因車禍身亡。父親瞞著媳婦帶著一家人開始逃難。媳婦只能喃喃表示一離開若丈夫回來找不到他們便無法團圓。
途中騾子死了,嬰兒死了,車架也毀損了,父親在夜色中將車子燒毀取暖,天亮後繼續前進;但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 賞析
二十歲時就以「蘋果」一片揚名國際影壇的莎米拉導演,從小在她的導演父親穆森.馬克馬爾巴夫的薰染下有了很好的表現,接著又拍了「黑板」以及這部在阿富汗拍攝的「下午五點」。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已遭受戰爭洗禮過的喀布爾。在失去一切的同時,藉著新舊思維的交替,強力介入探索伊斯蘭教義下被禁錮的婦女心靈。
女人的姿色在這個國度被認為是一種邪惡的誘惑,一般人均採取「眼不見為淨」來顯示自己未有邪念;這樣制式的反應不免令人有些難過。因為眼睛看見卻必須與意識相連結才會有「決定」,並非眼睛不見就能完全摒除這種誘惑的。
事實上伊斯蘭文化中婦女面罩下的那份思維,一直是很多人好奇的焦點;這自然是以西方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是在制約的同時,是否只能探索諾克奈及米娜這兩名二十歲與十二歲的女孩?
諾克奈必須以高齡和低齡的學童一起上學,透露了這個國家教育的不普及。而過去婦女所能接觸的書本應該也只限於可蘭經。諾克奈腳下的白色高跟鞋與洋傘是一
種抗拒的符徵,不管從美學觀點或心靈解放,諾克奈必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而開始有了新的思索。這是這部影片重要的訊息。
本片的結尾並不全然帶來預期的希望,不管是從政治的角度或民主的角度;甚至男女互動的文化思維,基本上都還是回到原點。
塔里班政權垮台後,美國的勢力開始介入,沙漠上的飛機與直升機是訊息的顯示,但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思考模式豈是剛剛碰觸的表相所能撼動?賓拉登與奧馬爾逃離阿富汗,事情與困境卻像大船擱淺一般在原地動彈不得。
戰爭之後被毀滅的城市依然棲息著這麼多孤苦無依的難民,他們沒有太多的奢想,只求在遼闊的大地上有個棲身之所。
諾克奈的父親讓人不禁想起「屋上的提琴手」裡那位窮困的猶太人爸爸,現實的困境幾乎將他逼入絕境,無奈只能對著上帝講話。諾克奈的父親可不敢如此造次,他選擇與騾子對話;這似乎是他唯一能在精神上尋找到的出口。
諾克奈代表著一種新的期許與希望,並大膽地挑戰著這個古老民族的禁忌與桎梏。號稱民主國家的美國至今尚未出現過女總統;但諾克奈大膽起了一個開端,換來的也許是陣陣的嘲弄與揶揄,但誰也難預測這個開始最後會不會開花結果?
米娜的死亡雖是意外,但給予這個議題相當大的震撼與打擊。同為競爭者的諾克奈在廢棄大樓的長廊上第一次脫下白色高跟鞋,光著腳自己玩著跳房子的遊戲。當
女總統與玩跳房子這之間的落差是多大?諾克奈感覺到一股從未有過的壓力襲擊而來,使她不得不退卻到孩童時期無憂無慮的心思。因為沒有欲望,似乎也就遠離了
生命的無常與恐懼。
詩人這個角色安插的略顯乾澀,然而我們不能以西方的男女互動觀念來對比詩人與諾克奈的感情,畢竟回教國家對男女之間的情感問題還是相當禁忌的。
藉著一位西班牙詩人的詩,譜出了下午五點這個關鍵詞。下午五點是過渡到夜晚的轉捩點,整首詩的意境充斥了悲觀與死亡,其實更恰當地說是在詮釋這個國度的
困境。當大地陷入完全漆黑時,單薄的意志與人力是輕如鴻毛,只能逆來順受,至於「女總統」的議題與希望,早就在父親焚燒車架的同時也一併火葬了。
不幸一再地降臨這個家庭。暗場人物的阿吉塔原本是這個家的希望,但最終上帝的旨意是讓他車禍而亡;雷諾瑪的嬰兒最終還是躲不過病魔的摧殘。爺爺抱著嬰兒
已經死亡多時的屍體慢慢地在荒野地用碎片挖一個小洞,然後將屍體埋入。生命在這兒永遠無法用天秤去衡量,因為這是一個現象,一種有時人類永遠都無法解釋與
自圓其說的現象。
其實影片一開始,導演就已界定了諾克奈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取代了兄長而擔負了家庭的瑣碎之事,這個面向也技巧地呈現了不同面貌的穆斯林家庭;更間接地提供了導演的企圖與主旨思想。
諾克奈遇上一名法國士兵,並由詩人擔任翻譯的戲,雖然呈現了諾克奈想當女總統的宏願,但其溶入的技巧似乎無法兼顧到結構的問題,尤其以對白來呈現缺乏了戲劇的張力,應是美中不足。
導演莎米拉的父親曾因拍過「坎大哈」一片而聞名於世。本片最終父親帶媳婦與女兒欲往坎大哈,是一種在絕望之後的一線希望,但尾場三人與唯一剩下的那頭騾子慢慢消失在高低不平的荒原時,仍留給觀眾許多失落與不安。
二十三歲的莎米拉拍出這樣令人驚異的電影,自然有著其背後的因素。不管如何,對於她大膽地到阿富汗拍了本片,這種冒險精神及尖銳的議題創作都是值得我們喝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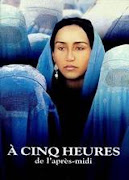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