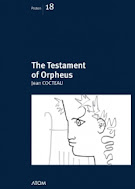 導演:詹姆.考克多(Jean Cocteau)
導演:詹姆.考克多(Jean Cocteau)
演員:詹姆.考克多(Jean Cocteau)
法國 / 1959年 / 77分鐘 / 輔導級
禮讚:1961英國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
一個18世紀的詩人,穿梭不同時空,探索生命與智慧的神秘…
◎ 劇情簡介
一名詩人的靈魂不斷地穿梭時空出現在不同的世代,有時他也會穿錯衣服而覺得尷尬。
首先他出現在一名教授前,見到教授已經病入膏肓,一名女護士推著他走,但護士見到詩人突然出現,驚嚇不已,而教授也在此時斷氣,手上一個裝子彈的小盒子掉落在地上,詩人便撿走了這個盒子。詩人又回到較早的空間,教授還是十三歲的小孩時期,小孩對詩人的出現相當困惑、好奇與驚訝。
詩人在野外道路上走著,卻跟一個馬頭人擦身而過,兩人各自有不同的情緒,不禁回頭互望。詩人決定跟蹤馬頭人,最終走入了一處廢墟,一群吉普賽人彈奏吉他,歌聲充滿了哀傷與悲鳴。詩人看見一名婦人從火堆中還原出一張相片,並交給一位女人,女人將相片撕成碎片然後交給詩人。
詩人一直對馬頭人沒有好感,但在海邊卻看見他以前電影中的演員從水中一躍而出,而演員賽潔斯帶他來到一幅畫前,兩人有一番的辯證,謂作品一直想謀殺創作的畫家,演員拿一朵木槿花讓詩人畫,但無論怎麼畫卻都畫出詩人自己。
於是詩人扮演學者,並將一朵撕爛的花還原。兩人一起去找科學與智慧之神。他們在一座舞台上打開一個木門,裡面一男一女象徵上帝的審判,開始質疑並控訴詩人,理由是他藐視司法而自認無辜,並控訴他以心靈侵入到另一個世界,詩人提出答辯,也提出電影的解釋,並重新詮釋了死亡的意義。因為電影是非現實穿上現實的衣裝;而透過死亡才能顯露真諦,但唯有詩人是永生不死的。審判官暫時接受了詩人的辯解,也示現了並無所謂真正的時空,而在這兒詩人也遇上了教授,但他們都被懲罰繼續活著。
詩人繼續向前行,卻在路上遇見了自己,但對彼此不打招呼相當責備。詩人也看見了一男一女的知識份子相互擁抱也頻頻為人簽名。然後詩人總是一直在等待要見某個人,最終在一殿堂上遇上雅典娜和隨從馬頭人,詩人被射殺,那群吉普賽人為他唱哀歌,於是詩人又從死亡復活,他向伊底帕斯王一樣目盲,但反看清了自己的靈魂。
◎ 劇情分析
以最精鍊的文字精準地詮釋所言所見,從而挑動或薰染了讀者的靈魂,那是非「詩」這種文種莫屬。詩藉著許多符號和象徵玩著比喻與想像的遊戲,敏銳地呈現四周氛圍的意象,一下對比;有時卻又類比,時而抽象;時而具體,透過這些文字的互動,詩人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於焉誕生。
短短幾行話,當然不足以去形容詩的意識形態與風格,只希望從這些引言中來探究考克多這位全方位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思維,從而進一步來碰觸「奧菲的遺言」這部電影整體的意旨與觀念。
與路易斯.布纽爾一樣被歸納在超現實理論的實踐者,但更多的線索可以指涉考克多其實是在電影中放置更多詩學創作與理論。「奧」片中採用詩人來回穿梭時空的趣味性,這提供了電影畫面的趣味性,當然也由此迸現了某些的象徵與創作力道。
深刻了解電影的拍攝原理,考克多以倒轉膠卷的原理,顛覆了時間的順敘,這屬於跳躍點狀的畫面,讓觀眾更有機會加入思索的空間。或許是這種強烈排列組合,躍動了觀眾的心靈訊息,於是考克多自己粉墨登場賣力演出,而觀眾卻得以在心性深處發掘了自我。
為何畫家臨摹一株木槿花,但畫出的卻是畫家自己?以這段為例,當知創作者必須結合意識與作決定的末那識才能創作出藝術佳品,而因每個人的第七識末那在累世中作了許多不同的決定,但因末那無法執持記憶種子而將之藏於八識如來藏,意思是當代許多出色的藝術家,他們絕非只靠今世的努力才成就這番藝境。但六識與七識共同合作創造藝術時,卻必須依賴本心如來藏這個持種心,也就是我們的真實心。雖然是這般詮釋,但卻不能誤解覺知心(六識與七識)是真心,只能說這二識及其他識都只是如來藏作用的一部份,畢竟真心是常住的心;而意識覺知心是虛妄生滅心。
知道唯識學這種詮釋立論,重新回來看畫家作畫總是繪出自我就能夠清楚理解了。以影片倒轉技巧可以讓人從海中復活躍起;也能讓一朵被撕裂的木槿花回復原狀。這個意題是泛指生死的面向,透過死亡,才能映照出復生的真諦。考克多在這兒所指的復生,並非指涉佛學的輪迴,而是「詩」的無拘無束。如果只在文字之間遊蕩,縱然詞句堆疊得宜,但就會缺乏詩的靈魂。而詩的靈魂乍現之後卻不能永遠駐足在原地,在消失與存在的辯證中,詩作是必然要經歷兩個極端的試煉,由此才能證明這首詩曾經被誕生、存在與思考。於是考克多藉了「死亡」的意象來傳遞「詩」在浴火之後,從死亡再度復生。
「弒父」是伊底帕斯這齣希臘神話中最重要的意旨,但這種觀念並非指世俗的不倫行徑,而是以詩為主體,從而對應了現實,而弒父就在瞬間轉變為「反叛傳統」。若無反叛,詩人勢必很難跳脫既定的窠臼,其創作便顯得一文不值。
事實上這也是後現代主義中「拼貼」與「並置」的手法,透過類比或對比,甚至看似無關的畫面,在依順序或一整體的表現,就會出現解構的動能,並在解構的同時,也會出現新的建構,於是原有的現象就不只是原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全新的氛圍與意象。而重要的是,這種新的詮釋觀點,正好呼應了這個世界本有的現象,只是在過去我們的思維並未如此仔細而能深入了解這一個面向。
奧菲的遺言不僅提及了人的現象;也企圖碰觸一個重要的議題-「我」的探索與困惑。生死是人類始終無法真正了解的議題,那是因為我們連自我都無法理解,更何況是去印證自我本心的存在與作用。考克多以伊底帕斯王和司芬克斯同時遇上詩人,古今人物並置當然是拼貼的手法,但伊底帕斯反映的是反叛傳統的弒父思想;而司芬克斯卻是提出「我是誰?」的困惑與執疑。從這兒我們也可理解詩人縱然能以象徵手法貫穿時空,企圖呈現「我」的永生不朽,而透過生死不斷地輪替,詩人的精神才能真正存在。以西方的哲學思考這種層面的展現屢見不鮮,但以「目盲」之後才得以展露新的契機,倒是少見的見地。考克多以雅典娜代表知性,而她卻射殺了詩人,然而詩人死亡後也以目盲之姿才得以見到世間的真相,亦即拋棄知性後死而復生,才能進入創作的空間。
維摩詰經云:「法離見聞覺知。」意即我們習慣以了知而自以為是的態度面對一切六塵,其實謂之為「顛倒之心」,因為世間所有事物都是根塵相觸後才能了知的,而這一切十八界的種種卻都是由第八識如來藏的妙明真心所出生,這樣的見地在楞嚴經卷二卷三敘述甚詳,不僅解釋了考克多未竟的困惑,也提供了真諦與隱藏的真相。
考克多的一心追索生命的真諦,但以佛學的觀點尚落入在「知」的見地中,別忘了「法離見聞覺知」這句話在在證實考克多只在「染法」中落實,雖然努力地想從各種現象中印證生命真相,但卻也只能在門外徘徊。
然而從電影藝術而言,考克多是極具細膩與智慧的,從影三十年最終在一九五九年完成此片,絕對是他以生命真正的告白,也讓我們見識了一位多才多藝的導演他心中真摯的吶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